國學與人生境界
來源:中國網 作者:袁濟喜 時間:2015年07月08日 人參與 評論 0 條 我要評論
當然,國學中的人生境界論是多元思想組成的。老子與莊子這些道家人物,對人生境界的理解與儒家有很大的不同。老莊認為人之所以不能取得自由,不能擺脫“人為物役”的悲劇,原因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受制于各種外物的束縛,只有將這些束縛人的“假我”、“非我”統統扔掉,人類才能走向自然,實現自身價值。在《莊子?大宗師》中,莊子假托顏回之口提出:“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道) 謂坐忘。”莊子用“心齋”、“坐忘”的心理特征說明人生境界的實現。中國文化與學術的內在生命力,比如對于自由情性的追求,對于高風遺韻的向往,都與老莊的人文精神有關。
老子與莊子所確定的這種人格本體主義在魏晉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其特點便是從思辨走向了現實的人格嚴肅主題。莊子揭露的弱肉強食,“無恥者富,多信者顯”的社會現象,到了漢末則愈演愈烈。魏晉文化與魏晉人格的永恒魅力,就在于這種社會場景中悲劇性地全面展開。這種追求又因了當時士族階層的崛起而形成為特定的人格,表現為后人津津樂道的“魏晉風度”。魏晉士族文人一方面風流自高,另一方面動亂又常常將他們拖入死亡。何晏、嵇康、陸機、陸云、潘岳、歐陽建、石崇等人,都是在動亂中被送上刑場的。這樣,就在強烈的人生追求與無可奈何的命運之間產生了尖銳的沖突。“死生亦大矣”,這是從莊子到魏晉名士痛感的人生主題。當人處于蒙昧階段,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價值時,還可以因麻木而減輕這種痛苦,但當人們有強烈的生命意識和生活欲望時,這種死亡就越發顯得驚心動魄。

魏晉風度 后世景仰
由此,對人生苦難的解脫,對逍遙境界的尋求,成了魏晉以來人生哲學的重大課題。正如湯用彤先生在《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一文中所言:“魏晉人生觀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為玄遠之絕對,而遺資生之相對。……從哲理上來說,所在意欲探求玄遠之世界,脫離塵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奧秘。”這段話與人們今天常引的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論魏晉人格瀟灑的話可以互相補充。漢魏以來,圍繞著人生的意義主題,各種哲學紛紛出現。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這樣幾種: 一種是以阮籍為代表的逍遙論;另一種是以嵇康為代表的養生論;再一種就是以《列子?楊朱篇》為代表的縱欲論。此外,還有何晏、王弼的無為論,向秀、郭象的安命論等等。魏晉以后逐漸興盛的佛教,則是從宗教麻痹的角度,來解釋人生問題的。隨著老莊與玄學的流行,人們對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路發出了挑戰,以自然的人格代替禮教人格。中國古代的人生境界論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高峰。而魏晉風度則這對于這一段時期思想文化的人格化與名士化。我在今年四月的《中華讀書報》上發表過一篇學術講演稿《魏晉風度與現代人生》,就是專門談這一問題的,在這里就不多說了。
中國古代的人生觀,雖然存在著儒道兩家的對立,但是這兩派的觀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互相補充的。儒家與道家都將人格境界奠定在農業社會的天人合一意識上,主張在與自然和諧相處中建構人格,而不是在與自然界的對立中建設人格,這就造成了儒道兩家文化人格的順從性與和諧性。儒家“與天地參”的道德境界,與道家的自然之道也可以相通,孔子晚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浴沂舞雩”的美境中獲得解脫,他的“浴沂舞雩”與莊子的“逍遙游”實質上是相同的,都是人生的自由境界。儒道兩家人格的不同有助于中國文化的活力與人生境界的多元化,他們彼此之間的互補,造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的廣博精深,中國后期受儒學熏陶的文化人物,沒有不出入佛老的,蘇軾、王夫之等人就是典型。
因此,談到中國人的人生境界,便不得不談佛教,尤其是禪宗的人生境界論。唐宋時期的禪宗思想,是中國人生境界論成熟的重要標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世俗的,他們不主張在脫離日常生活之外去追求西方人那種慘厲的宗教贖罪精神,因此,印度小乘佛教的教義與儀式很難在中國推行。禪宗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去參悟道。雖然它也有一套修煉儀式,如凈心寧意,排除雜念等等,然而其主流精神卻是倡導日常實踐以加強悟性,積累智慧。所謂“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禪宗不主張離開日常生活去思索佛性,而是力主禪境存在于日常的生活實踐之中,強調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之中皆有佛性在內,這是具有東方文化特點的泛神論思想。以往的小乘佛教在解釋三身法時,常常從外在偶像角度去解說,而禪宗則從自我心靈去倡論。而此種自悟具有豁然開朗的特性,所謂“忽遇風吹云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即是這種心理覺悟現象的表現。頓悟是禪宗獨特的精神領會方式,由于它是主觀和個體性的,又不脫對象的感性形式,心靈具有極大的創造性,與審美精神的釋放不謀而合。
禪宗常用三種境界來說明悟的境界。第一境是“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以喻精神的漂流,沒有得到禪境的指引;第二境是“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這是形容已經破除法執與我執,即超脫了客觀性相與主觀癡迷,使精神獲得一定的自由但尚未悟道;第三境是“萬古長空,一朝風月”,這是形容在頓悟中獲得永恒的體驗高峰,這雖是一霎那間的頓悟,但卻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永恒,禪境即是這種高峰體驗的產物。這種體驗由于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礎之上,是在與砍柴擔水,觀花賞月的平常生活相伴,因而它沒有出世的寂滅,與“高處不勝寒”的虛幻,相反,倒是充滿著日常生活的趣味,是一種恬淡閑和,平靜如水的心境。體現了中國文化一以貫之的寧靜而世俗的品格趣味。現代著名作家林語堂在《中國人》這本書中指出:“詩歌教會了中國人一種生活觀念,通過諺語的詩卷深切地滲入社會,給予他們一種悲天憫人的意識,使他們對大自然寄予無限的深情,并用一種藝術的眼光來看待人生。詩歌通過對大自然的感情,醫治了人們心靈的創痛,詩歌通過享受簡樸生活的教育,為中國文明保持了圣潔的理想。”這種詩學精神固然直接來自于中國傳統的儒道思想,但與禪宗的作用也是分不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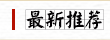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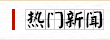

 浙公網安備 33102402000349號
浙公網安備 3310240200034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