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文脈的透視與梳理——讀《民國大學的文脈》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高有鵬 時間:2015年07月07日 人參與 評論 0 條 我要評論
先秦學者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其實就是文化建設,其中包括語言的規范。這是國家文化戰略的重要選擇。其邏輯結構在于語言文字是社會各個方面交流溝通的重要媒介,上通下達,統一語言文字,尤其是語言規范,便能夠統一意志。因而,現代文明面對國家文化戰略選擇的重大問題,同樣需要明確這樣一個目標。
1905年,科舉制度終結,新學興起;至1912年,新的國家建立,頒布《大學令》,繼而又有《大學規程》,中華民國政府把“文學”規定為“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和“語言學”三大科類。從“東京語”到“京城聲口”,到民國總統袁世凱為官話字母作“護法”,語文教育成為國家國民教育的制度。現代語文教育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全社會被形成一種共識,即“語言是造成民族的一種自然力量”。這句話在現代學術研究中被頻繁使用,那么,這是一句論斷,還是一句提示呢?近讀沈衛威《民國大學的文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他對這句話的闡述。此語出自《教部通令中小學校厲行國語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書,實行部頒國語標準》,可見于《民國日報》1930年2月3日載文。民國政府文化政策的解釋者稱:“各國都有標準語通行全國。我國自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議決以北平語為標準以來,各小學并不注意實行,仍以方言教學。我國人心不齊,全國人數雖多,竟如一盤散沙,毫無團結力量。這雖然不全是因為言語隔膜緣故,可是言語隔膜,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為此,懇請中央令教育部通飭全國中小學校在最短期間,厲行國語教育”,“前大學院曾經通令所屬各機關,提倡語體文,禁止小學采用文言文教科書。這是厲行國語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辦法,應由各該廳、局,一面遵照前令,切實通令所屬各小學,不得采用文言教科書,務必遵照部頒小學國語課程暫行標準,嚴厲推行;一面轉飭所屬高中師范科或師范學校,積極的教學標準國語,以期養成師資,這是很緊要的。望各該廳、局查照辦理。”
“國語教育”中“不得采用文言教科書”的意義是什么呢?是明治維新的啟迪嗎?是“我手寫我口”的呼應嗎?對于歷史文化問題,一切都應該用事實說話。沈衛威的學術研究在這里繼續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就是用歷史說明文化,在史料中間勾陳和甄別,找到文化的脈絡。應該說,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分野,并不是針鋒相對,也不應該是你死我活,其主要在于順應社會文化發展潮流。俗文學催生了新文學,唐宋白話從小說文本的意義上顯示出語言發展的必然趨勢。伴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文化失敗,即文化失望彌漫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越來越多的人堅定地選擇了新的語言方式。其實,這是文化發展的自我選擇,與新文學的潮流并沒有多少直接的聯系。但是,文化既然是有生命的,就需要引導。所以,新文學的搖旗吶喊,就形成了新的語言潮流;文言文作為“死了的”文化,一時間成為文化公敵。新文學與新文化被簡單定位于使用白話文,反對舊的文學和傳統文化,北京的“五四運動”形成這一高潮的峰巔。而唯獨南京,聚集著一批傳統語文即“國學”的堅定分子,與北京對峙。如胡小石曾經這樣總結當年的文學格局,說:“南京在文學史上可謂詩國。尤其在六朝以后建都之數百年中,國勢雖屬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學思想,多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傳統桎梏,而又富于創造能力,足稱黃金時代,其影響后世至巨。”的確,南京的文學成就,醒目于其獨特地勢興起的山水文學、文學教育、文學批評之獨立和聲律及宮體文學。王羲之家族在這里充當了文化領袖的角色,而且被不斷發揚光大。胡小石也應該知曉這里“桃花渡”的傳說,他引用《宋書·雷次宗傳》的記載,以歷史上的宋文帝元嘉十五年雞籠山開四館教學為此《學衡》文學格局源頭。雞籠山四館有雷次宗的儒學,何尚之的玄學,何承天的史學,謝元的文學,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史哲。東南文脈的起承轉合,躍然而出,由此也引發北京和南京兩大陣營的恩恩怨怨,貫穿在中國現代學術體系之中。東南形勝,其文脈傳承,綿延不絕,堅守著中國傳統文化,與新文學形成不同的態勢。胡小石稱“此與唐代自開元起以詩取進士,有同等重要”。似乎這種格局才是中國文化的命脈。這在總體上就給人以“新”與“舊”兩大陣營的印象。沈衛威在這兩種文化形態的沖突中,細致梳理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革命者等不同文化結構與類型的具體形成與轉變過程,更深刻挖掘《學衡》派文人的思想文化價值。與之前所不同的是,沈衛威更多了一些歷史的穿透,擴展開來,他引申向李四光等人的心理變遷,進行文化透視,展現出中國文化發展的軌跡。這是歷史文化的研究,也是社會生活的研究,主要是思想文化的研究。他把歷史文化的人物心理與時代精神研究相結合,展現與透視相結合,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新文學考據這一研究風格。許多問題被他展開,前后對比,相互對比,在對比中尋求精神脈絡的蛛絲馬跡。沈衛威著意勾勒出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一群教授王瀣、吳宓、胡先骕、黃侃、汪東、吳梅、汪辟疆、胡小石、胡翔東、王易所留下的大量的舊體詩詞曲,包括他們的《潛社詩刊》《潛社詞刊》《潛社詞續刊》《潛社曲刊》《潛社匯刊》《如社詞鈔》。這并不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繁榮與進步。尤其是沈衛威對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評選與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文化透視所做比較分析,指向中國傳統文化重的翰林制度,知識分子的心結形成新的矛盾沖突,更發人深省。
今天,這一命題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與時俱進,密切觀察當前變化萬端的文化發展,需要回答時代,其實也需要回答歷史,回應未來的呼喚。我們躲避不了現實,同樣回避不了歷史;用歷史透視現實,不僅能夠看得更遠,而且可以看得更清。現實與傳統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兩個階段,大的歷史構成歷史文化共同體,其中包含著對社會現實的支持與鼓舞。我們不合時宜地割裂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其實是一種虛無主義;當然,現實中有許多時代,在階段性中表現出時代的自我。《學衡》一派,其崛起與衰落,給我們許多啟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系,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離開了歷史傳統,或許我們就成了斷線的風箏。

- 上一篇:什么是“國學”
- 下一篇:光明時評:國學是社會不可缺失的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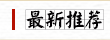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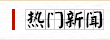

 浙公網安備 33102402000349號
浙公網安備 3310240200034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