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xué)與和諧天地
來源:中國網(wǎng) 作者:袁濟喜 時間:2015年07月10日 人參與 評論 0 條 我要評論
原標題:《國學(xué)十講》第十講:國學(xué)與和諧天地
主講人:袁濟喜
國學(xué)作為“一國固有之學(xué)術(shù)”,凝聚著中華文化精神及其形態(tài),而和諧之道乃是國學(xué)不同于西學(xué)的重要標志,要了解國學(xué)與中華文化精神,必須對于和諧文化的奧秘進行分析與探索。
一、和諧之道與中華文明
如果我們將和諧作為中華文明與西方崇高沖突對立文化精神相異的核心理念,我們首先必須承認,這種文化精神與文化心理,是植根于我們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古代形態(tài)的,并不是哪位圣人先知先覺的產(chǎn)物。
人類最早的文明形態(tài)是從賴以生存與繁衍的自然界生態(tài)環(huán)境生成與發(fā)展而來的。中國遠古先民遍布于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依賴農(nóng)耕、漁獵來自我生存、自我發(fā)展,環(huán)繞他們周圍的是天地自然。在長期的艱苦生存中,初民直觀地感到自然界的和諧相生是基本的條件。宗白華先生在《美學(xué)散步》中指出:
希臘半島上城邦人民的意識更著重在城市生活里的秩序和組織,中國的廣大平原的農(nóng)業(yè)社會卻以天地四時為主要的環(huán)境,人們的生產(chǎn)勞動是和天地四時的節(jié)奏相適應(yīng)。
這段話對于我們理解中華文明為何追求和諧之道是至關(guān)重要的。孔子曾贊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在孔子看來,蒼穹籠蓋四野,覆育人類,四時更替,百物繁興,這一切多么和諧,然而它又絲毫不露造物的痕跡,這就是最高的和美。荀子盛贊天地?zé)o自然的和諧魅力。他說:“列星隨旋,日月遞熠,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fēng)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荀子•天論》)荀子認為,自然界本身的和諧相生,四時交替,這就是“神”,不存在先天的造物主,荀子用自然和諧之“神”的觀念,替換了殷周宗教的有神論。
儒家將天地的和諧有序,上升到宇宙規(guī)律的高度來推崇,認為這種規(guī)律表現(xiàn)了至中無偏的本性。《中庸》一書的作者反復(fù)倡言: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作者認為,“中”與“和”是宇宙的秩序與法則,這種自然的法則與人類社會的法則是相通的,因此,他們又將人類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用來說明白然界的存在。春秋時的鄭國子產(chǎn)就提出:“夫禮,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荀子說得更為直接:“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jié),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荀子•禮論》)荀子直觀地將天地之序與禮義秩序相印證,從“天和”推論到“人和”,以此證明天人合一的哲學(xué)觀。
道家與儒家相比,更欣賞大自然的和諧相生,并且把這種美稱之為“大美”。老子將自然作為人類行為的準則,人事必須以自然作為歸依。他提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而理想人格圣人行事,體現(xiàn)出以自然為宗的美德,他們功成身退,百姓以自然美德譽之。所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第十七章)就是這種美德的表現(xiàn)。在老子書中,以自然為模則,通過觀察自然,效法自然,進而確立人事法則,成了一貫的思維方式與基本原則。莊子也秉承了這一觀念,他說:“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jié),萬物不傷,群生不失,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莊子•繕性》)莊子贊嘆,遠古社會,天人處于混茫一體之中,陰陽和靜,四時和諧,自然界呈現(xiàn)出一幅安寧靜謐的景象。從自然的和諧中觀察天地之美,這是道家的基本思想,它在魏晉南北朝得到了廣泛的發(fā)揮。如阮籍的《達莊論》就說:“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東晉名士蘭亭修禊時所寫的詩歌,大都抒寫贊美自然的愉悅之情。其中王羲之的兩首詩最具代表性:“悠悠大象運,輪轉(zhuǎn)無停際。陶化非吾因,去來非吾制。”“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鈞。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在他們看來,自然的和諧相生是宇宙之“道”的顯現(xiàn)。
到了孔子論中和,總結(jié)了前人思想的精華而加以發(fā)展。孔子論和諧,主要從中庸談起。中國古代自殷周以來,就倡導(dǎo)一種居中不偏,恪守道德秩序的品行。這是因為在農(nóng)業(yè)社會中追求天行有常的自然秩序,同時倫常有序的血緣宗法成為社會的紐帶,因而恒久與執(zhí)中就成為維系這種社會秩序的基本道德標準,也是禮度的必然要求。對統(tǒng)治者來說,遵守中庸,反對過分聚斂,也是維護自己統(tǒng)治的根本。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禮崩樂壞的一個表現(xiàn)就是人們行事沒有道德約束,肆無忌憚,好走極端,所以孔子認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禮記•中庸》記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孔子論君子人格時還說:“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在這里指君子所應(yīng)具備的各種各樣的文化修養(yǎng),宋代司馬光說:“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答孔文仲司戶書》)可見這種“文”包含了美的修養(yǎng)在內(nèi),而這種美的文化修養(yǎng)又是通過“六藝之教”的途徑獲得的。在孔子看來,質(zhì)主要是指一個人的道德品質(zhì),而文則是指他的文化修養(yǎng)與文明程度。質(zhì)勝于文,就會使人顯得粗野,可見光有質(zhì)還不行,還必須有相應(yīng)的文飾。孔子一般說來,是倡導(dǎo)那種溫良恭儉讓的品格修養(yǎng)的。
但我們在這里特別強調(diào)的是,孔子論中和,并不僅僅是調(diào)和的意思,他更強調(diào)的是一種和而不同,以及通過真實直率來解決矛盾的思想。孔子首次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子所說的“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也就是在堅持原則的基礎(chǔ)之上,要有所差異與不同,這是君子與人交往的原則;而“同而不和”、“周而不比”,就是不分是非,以利益為轉(zhuǎn)移,是小人之間交往的特征。孔子的弟子有子曾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這句話通常只被人們引用前幾句,而實際上后面的意思是說,如果只是一味為和而和,放棄禮義準則,這是絕對不可行的。
從人格標準來說,孔子認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他還說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可見孔子本是疾惡如仇,憎愛分明之人。當然,孔子也提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可見成人之美在孔子看來是一種美德,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放棄原則,不敢得罪人。孔子論君臣之和時,特別強調(diào)直言敢諫的精神,他提出:“事君之道,勿欺之,可犯之。”也就是說,臣下對于君王,可以犯顏直諫,而不能欺騙他。孔子明確反對以德報怨,提倡以直報怨。他提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微子》中記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孔子對于敢于觸犯商紂王這樣的暴君的三位直臣加以贊嘆,稱他們這仁者。而反對那種好好先生。他說過:“鄉(xiāng)原,德之賊也。”什么是鄉(xiāng)愿呢,孟子對于此有過解釋:“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也就是說,有一種人,別人對他既不說出好來,也挑不出壞來,外表圓滑,同流合污,這就是鄉(xiāng)愿。這樣的人是孔子堅決不認同的。
至于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孔子更是加以直斥:“巧言令色,鮮矣仁!”認為這樣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是仁者。《論語》中還記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直言,對于左丘明《春秋》中批評的那些巧言令色、虛偽狡詐之徒,他也同樣厭憎。孟子曾分析孔子為什么有時鼓勵狂狷即極端的行為,實在是當時不得已的行為。孟子說:“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這種分析是很中肯的意見。
孔子論君臣之道如何算作真正的和諧之道的思想,直接影響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培育了中國后來那些類似海瑞那樣的直臣與諍臣。《貞觀政要》的第一篇《君道》中記載: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征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圣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異,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魏征與唐太宗通過對于歷史上的明君與昏君的比較,得出了必須“兼聽納下”的為政之道,這里面顯然是吸取了中國古代‘和而不同“的思想。這種和諧之道尤其是我們今天建立政治文明所需要發(fā)揚光大的。在今天的社會中,和諧之道常常被曲解為一團和氣,掩蓋矛盾,這是與傳統(tǒng)的和諧之道根本不相干的。
中國古代哲人論和諧的另一個重要觀念,便是從對立統(tǒng)—之中去看待自然界的和諧,這便是《周易》中系統(tǒng)論述的陰陽剛?cè)嵊^念。《周易》中反復(fù)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而剛?cè)嵊畜w,以體天地之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嗣后,“兩一”觀念在古代哲學(xué)與美學(xué)中便成為基本范疇,也是人們論“中和”的邏輯出發(fā)點。如《呂氏春秋•大樂》云:“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更合,合則復(fù)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fù)始,極則復(fù)反,莫不咸當。”作者強調(diào),事物的和諧是兩極的統(tǒng)一,和諧最終又被矛盾所打破,形成新的矛盾統(tǒng)一體,這是從運動的過程來看待和諧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定勢》篇中提出“剛?cè)犭m殊,必隨時而適用”,“然文之任勢,勢有剛?cè)?rdquo;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關(guān)于陽剛陰柔之美的論述是很有名的。其中的理論依據(jù)便是《周易》中的陰陽剛?cè)釋W(xué)說。
古人論“和”,往往又將陰陽剛?cè)崤c“氣”的觀念相結(jié)合。古代哲人把“氣”作為萬物與自然的基本要素與功能。“氣”蘊含陰陽二極,陰陽之氣的交合,化生出天地的理想狀態(tài),這便是“和”。道家的創(chuàng)始人老子說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認為陰陽二氣的沖和組成了萬物的和美。《淮南子•汜論訓(xùn)》指出:“天地之氣,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diào),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太剛則折,太柔則卷,圣人正在剛?cè)嶂g,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生和。”《淮南子》作者從天地陰陽之氣的沖和談到圣人秉受剛?cè)嶂裕闷?ldquo;中和”之氣。陰陽之和既是理想的人格,也是審美的最高層次。這一觀點也為東漢王充所繼承。王充在《論衡》提出,天地陰陽之氣和諧相生,便成和氣,于是產(chǎn)生祥瑞之物:“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凰、麒麟,亦和氣所生也。”王充把陰陽調(diào)和視做善與美的基本條件,直觀地認為和氣生美物,而戾氣生邪物。宋儒從宇宙發(fā)生學(xué)的角度提出:太和是陰陽二氣未分、宇宙混瀠一片時的本根,通過“道”的變化而產(chǎn)生陰陽二氣以及萬物。北宋思想家張載說:“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組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末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太和》)張載認為“太和”即所謂“道”是宇宙的始基,它由陰陽二氣化生交感,產(chǎn)生出宇宙間萬物,又由陰陽綱組造成自然萬物的和諧有序,其始也幽微莫測,其究也成就堅固廣大的一切形體。這也是一切生命之“氣”的運動與變化法則。
在古人哲人看來,和諧是歸根結(jié)底是一種人生的幸福論。天地自然的和諧之美,不僅體現(xiàn)了自身的秩序性和規(guī)律性,而且這種“和”具有目的論的意義,即自然向人生成的倫理意義,這是古人論“中和”的基本看法。《周易》中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賦予云行雨施、品物流行的天地以生養(yǎng)萬物、惠澤人類的人情味道。春秋戰(zhàn)國以來,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科技的進步,以及以人為本思想的活躍,主體論的美學(xué)得到極大的發(fā)展,在孔孟、老莊那里都有不同的表現(xiàn)。《呂氏春秋》作為一本兼容并包的雜家著作,糅合儒道兩家的主體論人學(xué),在美學(xué)中倡論以心為本的思想。作者提出: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樂。心必樂,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wù)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適。
《呂氏春秋》的作者認為人從生理常規(guī)來說,都是貪圖美聲美味美色等等的,但是人的生理欲求畢竟不等于人性的最高境界,所謂“心”也就是主體的思想與情感,決定了人對外界事物刺激的接受與感應(yīng)的態(tài)度。當人心處于憂愁或煩悶時,外界的事物就不可能對人構(gòu)成審美對象。要使審美的主客體和諧一致,必須使主體處于一種和諧快樂的地步,這樣才能使主體得到快樂,同時也使審美對象的價值得以實現(xiàn)。
國學(xué)的和諧天地,在中國古代的文藝中,達到了極致。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不但注重從不同中求勻稱,更推崇從均衡中求變化,在審美境界上更是以天工自然、和諧平淡為圭臬。在中國古代,美的和諧往往用“文”來表示,它包含自然界、社會生活領(lǐng)域一切色彩絢麗、富有藻飾的事物,而“文”的組成則是由諸多因素構(gòu)成的。《說文解字》云:“文,錯畫也,象交文。”意即文是由不同的線條交錯而成的一種美的視覺形象。《易傳•系辭》說:“叁伍以變,錯綜其數(shù),通其變而成天下之文。”《楚辭•橘頌》說:“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禮記•樂記》說:“五色成文而不亂。”王充《論衡》也說:“學(xué)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到了六朝的劉勰著《文心雕龍•情采》篇,進一步發(fā)揮了這種觀點,把雜多因素的組合視為和諧與美的根源:“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fā)而為辭章,神理之數(shù)也。”所謂“神理之數(shù)”,也就是自然之道。類似這樣的觀點在古希臘美學(xué)中也普遍存在。如赫拉克利特就指出:“自然是由聯(lián)合對立物造成的和諧,藝術(shù)也是這樣。如繪畫混合著白色和黑色、黃色和紅色,音樂混合著不同音調(diào)的高音和低音、長音和短音。”不過西方人強調(diào)和諧中的對立,而中國古代文人更注重對立面和諧的轉(zhuǎn)化,追求總體和諧之美。
與書畫相通的詩文聲律對偶之美,也體現(xiàn)著“和而不同”的創(chuàng)造原則。詩歌的聲解不僅是有助于諷誦,更主要是便于吟詠情志,抒寫性靈。西晉陸機《文賦》談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錆而難便。茍達變而識次,猶開流而納泉。如失機而后會,恒操末以續(xù)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洪澀而不鮮。”陸機認為音聲的迭變是逝止無常的,作文須掌握音韻的自然變化,作有機的組織和安排。而音律由不同的音節(jié)迭變構(gòu)成,“若五色之相宣”。
在小說美學(xué)領(lǐng)域,古人也強調(diào)“和而不同”。中國古典小說,尤其是明清以來的章回小說,注重敘事性,情節(jié)以單線條為主,通過情節(jié)的鋪敘展現(xiàn)人物的性格。由于小說故事情節(jié)的繁多,難免會出現(xiàn)“似曾相識”的現(xiàn)象。像《西游記》這樣的神魔小說,主要敘述孫悟空大鬧天宮以及保護唐僧西天取經(jīng)的各種故事,這些故事單獨成篇又互相連貫,其間免不了要產(chǎn)生“犯”即雷同的現(xiàn)象。為了求得故事的生動活潑、吸引讀者,一方面必須使情節(jié)故事互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如果在相同的故事中寫出不同的人物性格,達到“和而不同”的效果,則更為高明。因為情節(jié)是為塑造人物性格服務(wù)的。金圣嘆在批《水滸傳》第十一回時提出“將欲避之,必先犯之”,也就是說,要避免雷同,就先要寫相同的事件,在同中求異,從而既互相應(yīng)和又各不相同,增強小說的趣味性和讀者的美感。如《水滸傳》中同是打虎,武松打虎與李逵殺虎不同;同是殺嫂,武松殺嫂與石秀殺嫂不同;同是劫法場,江州劫法場和大名府劫法場不同;同是因?qū)毜渡拢譀_買刀與楊志賣刀不同等等,都是相同的事件卻寫出不同的人物個性,衍變出不同的意味情思,這都是“犯”而后避、“和而不同”。清代的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也談到:“作文者以善避為能,又以善犯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無所見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見其能避也。”毛宗崗總結(jié)了《三國演義》敘事與塑造人物的技巧與方法,指出《三國演義》善于寫出相同事件中的不同特點來。比如對火的描寫,是寫兵家常用的攻戰(zhàn)方式,“呂布有濮陽之火,曹操有烏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陸遜有獍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盤蛇谷、上方谷之火”,但它的寫法卻情態(tài)各異,意趣盎然,在應(yīng)和中又各具特色,沒有雷同重復(fù)的感覺。所以《三國演義》一書,“譬如樹同是樹,枝同是枝,葉同是葉,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結(jié)子,五色紛披,各成異采。”
當然,中國歷史上許多優(yōu)秀的文藝家,在特定情境下,往往打破中和,以狂怪沖突之美獲得獨立價值。明代李贄就大聲呼吁:“且吾聞之:追風(fēng)逐電之足,決不在于牝牡驪黃之間,聲應(yīng)氣求之夫,決不在于尋行數(shù)墨之士;風(fēng)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jié)構(gòu)之密,偶對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yīng),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雜說》)李贄認為真正的文章,決不拘守于“首尾相應(yīng),虛實相生”之類的法度,而是天工自然,臻于“化境”,一切形式上的“和”都溶人自然之道,“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湯顯祖也說:“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合奇序》)清代石濤更是提出:“無法之法,乃為至法。”(《畫語錄》)他們都反對因襲前人之法而不知有我。總之,中國古代有成就的文藝家認為,達到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和諧需要一定的法度,但是這種法度應(yīng)以自然為準則,并運以藝術(shù)家的獨特個性,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氣韻天成、和諧完美的作品來。
二、對和諧之道的重新反思
當然,古代社會已經(jīng)過去,畢竟我們今天生活在21世紀之中,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年代,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中,對于傳統(tǒng)的和諧之道當然必須進行全面的反思。如果沒有清醒的反思,重建和諧文化便無從談起。
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走著不同的道路。歐洲文明起源于古希臘雅典城邦之中。古希臘的雅典從地理環(huán)境上來說,與大陸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環(huán)境不同。這個半島周圍有良好的港灣,可以通向愛琴海的群島,甚至直達小亞細亞。從公元前十二世紀到八世紀,古希臘的雅典一直處于土地貴族統(tǒng)治下,其后經(jīng)過各部落的不斷聯(lián)系,尤其是一系列政治改革后,逐漸確立了按階級和財產(chǎn)關(guān)系劃分人口的社會形態(tài),開始取代氏族血緣關(guān)系基礎(chǔ)之上的社會制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論梭倫改革時指出:“這樣,在憲法中便加入了一個全新的因素一私人所有制。國家公民的權(quán)利一義務(wù),是按他們土地財產(chǎn)底多寡來規(guī)定的。有產(chǎn)階級既開始獲得了勢力,于是舊的血緣親族關(guān)系的集團就開始被排斥了,氏族制度又遭受了新的失敗。”而此時的中國周朝,正演出一幕制禮作樂,按血緣宗法關(guān)系封邦建國的活劇。以土地為經(jīng)濟基礎(chǔ)的氏族統(tǒng)治的削弱,帶來的是古希臘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以及移民的興起,其范圍已被及周圍的鄰國。在奴肅制經(jīng)濟繁榮的基礎(chǔ)上,雅典的公民民主制度也發(fā)展成熟起來了。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變?yōu)榉傻钠跫s關(guān)系,它無需溫情脈脈的親族關(guān)系來“和同”,人與自然也無需通過群體來契合天道,實現(xiàn)天人合一。荷馬史詩中的奧德修斯在與大海等惡劣的自然條件搏斗中,歷盡艱辛,回到家鄉(xiāng),依靠的是個體的力量;普羅來修斯敢于觸犯天條,表現(xiàn)了一往無前的英勇氣慨。
古希臘的悲劇精神,是在個體自由發(fā)展,同時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尖銳對立中展天的。因為對于每一個人來說,擺脫了土地氏族社會血緣和等級制度的束縛,固然取得了個體自由發(fā)展的機緣,但同時也使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失支了群體的依托,受到無數(shù)不可捉摸的偶然性的支配,由此滋生了頭腦中的命運觀念。古希臘著名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有一段歌詞道出了人們對無情世界的困惑不解:“朋友呵,看天意是多么無情!哪有天恩扶助蜉蝣般的世人?君不見孱弱無助的人類,虛度著如夢的浮生,因為不見光明而傷悲?啊,無論人有怎樣的智慧,總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朱光潛先生在《悲劇心理學(xué)》中論古希臘悲劇精神時說:“從整個希臘悲劇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它們反映了一種相當陰郁的人生觀。生來孱弱而無知的人類注定了要永遠進行戰(zhàn)斗。而戰(zhàn)斗中的對手不僅有嚴酷的眾神、而且有無情而變化莫測的命運。他的頭上隨時有無可抗拒的力量在威脅著他的生存,象懸?guī)r巨石,隨時可能倒塌下來把他壓為齏粉。他既沒有力量抗拒這種狀態(tài),也沒有智慧理解它。他的頭腦中無疑常常會思索惡的根源和正義的觀念等等,但是很難相信自己能夠反抗神的意志,或者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個體孤獨感與命運感,表現(xiàn)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沖突不和,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底蘊。中世紀希伯來文明的輸入,也沒有消融與取代自古希臘以來形成的悲劇精神,而是使這種悲劇意識轉(zhuǎn)化為新的文化形態(tài)。希伯來的宗教精神,將靈與肉、個體與宇宙的裂變變得更為嚴重,雖然在虛幻的宗教天國中,一切變得至美至善,因而中世紀美學(xué)以和諧完善為美。但宗教以人生苦難換取天堂的慰藉,本身就是一種悲劇。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中指出:“宗教的苦難既是現(xiàn)實的苦難的表現(xiàn),又是對這種苦難的抗議。”歸根結(jié)底,它是極度的人世不和諧與悲劇所造成的精神異化現(xiàn)象,這正如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shù)之于當時的人生苦難一樣。
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悲劇人生觀在文藝復(fù)興時期的巨匠莎士比亞、米開朗基羅那里得到了充分表現(xiàn)。隨著啟蒙時期人文主義精神的逝去,以叔本華、尼采學(xué)說為代表的悲劇人生觀彌漫西方世界。在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看來,古希臘是一個陽光燦爛、海風(fēng)拂煦的和諧社會,法國藝術(shù)史論家泰納的《藝術(shù)哲學(xué)》就說:“希臘是一個美麗的鄉(xiāng)土,使居民的心情愉快,以人生為節(jié)日。”他在書中所描繪的古希臘時期的文藝狀況與人生情景經(jīng)過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優(yōu)美暢達的文筆的譯述,曾經(jīng)為中國許多讀者為之神往心馳。但尼采卻獨具只眼地看到了古希臘人的悲劇精神,其日神說與酒神說對現(xiàn)代西方的美學(xué)產(chǎn)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作用,西方人始終認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不存在什么天人合一、人人和一的可能性,貫穿于西方文化的內(nèi)在精神,是沖突不和的悲劇人生觀。西方文化過度強調(diào)人與自然的沖突,造成工業(yè)革命后人與自然的尖銳對方,現(xiàn)代社會的種種弊端,實與這種文化觀念有關(guān)。
而中國人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綜上所述,以中庸和諧為指歸,追求天人之間的和諧一體,這對于克服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弊端有著矯正的作用。但是,中國人的和諧觀念確實也有追求大團圓與虛幻境界的缺弊。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指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非是而欲厭(滿足)閱者之心,難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其最著之一例也。”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更是尖銳地指了:“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傳統(tǒng)的和諧觀念,客觀上對于國民性的怯懦與保守,產(chǎn)生了一些消極的作用,這是不用諱言的。近代以來,中國的大門被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大炮轟開,隨著封建自然經(jīng)濟形態(tài)的更替,專制制度的解體,以及一浪高過一浪的西方文化的沖擊,包括中和在內(nèi)的中國古典美學(xué)體系也受到挑戰(zhàn)和批判。“五四”之后,中國文化也在不斷地吸收西方文明過程中,痛苦地尋覓著、探索著,盡管它可能會遭受種種曲折,但是,在東西方文化的沖撞、交流中,中華文明中和諧理想的重建卻是勢所必然的。中國當今的和諧之道,在政治與經(jīng)濟改革的不斷深入之中,隨著中國現(xiàn)代化的推進與現(xiàn)代性的建立,必然會獲得重新建構(gòu),再續(xù)輝煌。這將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世紀工程,而國學(xué)的意義將通過此而得到彰顯與激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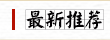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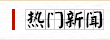

 浙公網(wǎng)安備 33102402000349號
浙公網(wǎng)安備 3310240200034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