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guó)學(xué)大師的人文情懷
來源:中國(guó)網(wǎng) 作者:袁濟(jì)喜 時(shí)間:2015年07月10日 人參與 評(píng)論 0 條 我要評(píng)論
原標(biāo)題:《國(guó)學(xué)十講》第八講:國(guó)學(xué)大師的人文情懷
主講人:袁濟(jì)喜
中國(guó)傳統(tǒng)的人文學(xué)術(shù)即國(guó)學(xué),始終將學(xué)術(shù)與人格境界融為一體,充滿著人文情懷,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臘起就形成的學(xué)術(shù)觀念,后者注重學(xué)術(shù)的工具性,而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探索如何與天地之道、社會(huì)人生的結(jié)合,追求學(xué)術(shù)中真善美境界的融合,從亞理士多德與孔子學(xué)術(shù)價(jià)值觀的比較中,便可以見出這一點(diǎn)來。亞理士多德倡導(dǎo)學(xué)術(shù)的工具性,而孔子教育學(xué)生時(shí)卻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說:“士,志于道”;《禮記•中庸》中提出學(xué)習(xí)的境界為:“博學(xué)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明代東林黨人顧憲宗提出:“風(fēng)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guó)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便是這種讀書求學(xué)與天下之事相關(guān)聯(lián)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觀的體現(xiàn)。真正的學(xué)問,往往是在這種情懷熏陶下形成,并且通過個(gè)體人格的堅(jiān)毅實(shí)踐來造就的。在這一講中,我們通過對(duì)于幾位近代國(guó)學(xué)大師人文情懷的介紹,來探討國(guó)學(xué)的這一特點(diǎn)。
一、章太炎的漢語情結(jié)
章太炎是近代國(guó)學(xué)的宗師,他對(duì)于當(dāng)代的國(guó)學(xué)思潮影響至大至深。因此,要談國(guó)學(xué)大師,是不能回避太炎先生的。章太炎早年走的也是純正的清代學(xué)者的道路,他年少時(shí)在杭州西湖邊上的詁經(jīng)精舍師從俞樾學(xué)習(xí)經(jīng)學(xué)與小學(xué)。但近代風(fēng)起云涌的維新思潮與革命運(yùn)動(dòng),促使他走出書齋,訣別俞樾。他將自己的學(xué)問與實(shí)踐結(jié)合起來,他的學(xué)生魯迅先生稱他為“有學(xué)問的革命家”。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國(guó)粹學(xué)報(bào)》上發(fā)表若干學(xué)術(shù)文字,并在東京開設(shè)國(guó)學(xué)講習(xí)班,“宏獎(jiǎng)光復(fù),不廢講學(xué)”。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編同盟會(huì)的機(jī)關(guān)報(bào)《民報(bào)》時(shí),刊登《國(guó)學(xué)振興社廣告》,仿效日本一些學(xué)者用“一國(guó)固有之學(xué)問”來弘揚(yáng)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國(guó)學(xué)講習(xí)班培養(yǎng)了許多國(guó)學(xué)大家。后來北京大學(xué)一些著名的文科教授,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門下。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壇,在蘇州主持章氏國(guó)學(xué)講習(xí)會(huì),主編《制言》雜志,培養(yǎng)國(guó)學(xué)人才。
梁?jiǎn)⒊凇肚宕鷮W(xué)術(shù)概論》中指出:“在此清學(xué)蛻分與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為正統(tǒng)派大張其軍者,曰:余杭章炳麟。”在晚清學(xué)界新舊交替之際,章太炎呼吁:
夫國(guó)學(xué)者,國(guó)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jìng)爭(zhēng)之世,徒恃國(guó)學(xué)固不足以立國(guó)矣。而吾未聞國(guó)學(xué)不興而能自立者也。吾聞?dòng)袊?guó)亡而國(guó)學(xué)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guó)學(xué)先亡而國(guó)仍立者也。
章太炎告誡人們,當(dāng)此國(guó)運(yùn)日危、文化轉(zhuǎn)型之時(shí),光靠國(guó)學(xué)固然不足以立國(guó),還要充分學(xué)習(xí)西學(xué),但是國(guó)學(xué)不振而要復(fù)興中華卻是絕無可能的。
章太炎在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學(xué)答問》中,上探語源,下明流變,頗多創(chuàng)獲。他從漢語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點(diǎn)出發(fā),論證國(guó)文的基礎(chǔ)是漢語獨(dú)特的語言文字形態(tài),不同于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體系,這是卓有識(shí)見的。我們知道,漢字的單音獨(dú)體,造就了漢語寫作的聲律之美,同時(shí),漢語的象形寫意的特點(diǎn),使得漢語文章具備形象直觀,抒情言志的的價(jià)值觀念,是人格精神與審美精神的寄托與表達(dá),通過“神”、“氣”、“音節(jié)”、“義法”等概念加以表述,與西方語言文章寫作有著很大的不同。
章太炎對(duì)小學(xué)的研究超越了傳統(tǒng)乾嘉樸學(xué)的樊籬,將小學(xué)從經(jīng)學(xué)中解放出來,將其提升到一個(gè)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強(qiáng)調(diào):“蓋小學(xué)者,國(guó)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故而“以為文學(xué)故訓(xùn),必當(dāng)普教國(guó)人。”也就是說,以研究語言文字為中心的傳統(tǒng)小學(xué),是研究漢語文化的出發(fā)點(diǎn)與基礎(chǔ),倡導(dǎo)國(guó)學(xué),首先要從小學(xué)入手。他自己的治學(xué),由小學(xué)入門,主張音韻文字相通,以此為基礎(chǔ),結(jié)合西學(xué),恢弘清代諸子學(xué)之門戶,其方法已經(jīng)超越了老師俞樾。他杰出的學(xué)術(shù)成就,也證明了這條治學(xué)路徑的可行性。
章氏的文字理論,提出一個(gè)“孳乳”的概念,他強(qiáng)調(diào)漢字不僅是工具,更是本體,是不可替代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現(xiàn)在中華民族語言的獨(dú)立性上。如果中華民族離開了這種安生立命的文字與語言,那就要崩潰。
在20世紀(jì)初“華夏雕瘁,國(guó)聞淪失,西來殊學(xué),蕩滅舊貫”的中國(guó),國(guó)學(xué)與西學(xué)的沖突異常激烈,學(xué)術(shù)界一些人士將漢語漢字作為舊的工具,急于在語言文字上與西方接軌。吳稚暉力推“萬國(guó)新語”,痛斥漢語文字“野蠻”、“無效率”;康有為幻想理想中的“地球萬音室”,對(duì)語言文字的取舍十分直截爽快:“夫語言文字,出于人為耳,無體不可,但取易簡(jiǎn),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數(shù)學(xué)、律學(xué)、哲學(xué)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須也,故以刪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為要義。”胡適的學(xué)生傅斯年則提出文字只是工具而已:“文字的作用僅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沒有絲毫作用嗎?我答道,是的,我實(shí)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僅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個(gè)方便”,甚至嘲笑“造字的時(shí)候,原是極野蠻的時(shí)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一直保持到現(xiàn)代的社會(huì)里,難道不自慚形穢嗎?……哼!這是國(guó)粹!這要保存!好個(gè)萬國(guó)無雙的美備文字!”這些說法難免有些激進(jìn)與幼稚。
當(dāng)時(shí),一些“五四”急進(jìn)派圍攻漢字的呼聲四起,中國(guó)的語言文字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章太炎堅(jiān)持不為所動(dòng),他強(qiáng)調(diào)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或可說是本質(zhì)。他在系統(tǒng)的論證中,再三論述了這個(gè)語言文字體系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古字至少,而后代孽乳為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字雖轉(zhuǎn)繁,其語必有所根本。”正是因?yàn)橹袊?guó)的語言文字是這樣富有中國(guó)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統(tǒng),章太炎才從其中發(fā)掘資源,構(gòu)造一個(gè)“依自不依他”、具有自覺精神的文化主體。章太炎認(rèn)為,文化亡則國(guó)家必亡,即使一朝國(guó)破,文化血統(tǒng)流傳在國(guó)人心中,那么復(fù)國(guó)也就指日可待。從中不難看出他如此強(qiáng)烈的人文情懷與民族意識(shí)。
在章太炎看來,新的語言資源大可從我們就有的豐富宏博的方言中取得,沒有承前,必不能啟后。更難能可貴的是,章太炎積極地身體力行自己的學(xué)說主張,編制了一套36個(gè)聲母,22個(gè)韻尾的標(biāo)音方案,后由錢玄同等弟子發(fā)揚(yáng)推廣。章太炎在艱辛著述的《新方言》中,利用中國(guó)語文的聲音古今相禪的特性,用“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疑于聲者,以義正之”的著作方針,來實(shí)踐他建設(shè)現(xiàn)代語文的主張,他明白對(duì)于舊有的文化資源必須慎之又慎,當(dāng)狂熱的西學(xué)大潮席卷滌蕩古老的文明,過快的車輪也許會(huì)盲目的碾碎一切,這時(shí),必須有悲劇英雄去阻擋,以攔住這受驚狂奔的飚車。
章太炎并不反對(duì)白話文的運(yùn)用,他曾在浙江省教育會(huì)上說:“將來語言統(tǒng)一之后,小學(xué)教科書不妨用白話文來編。”他也深知當(dāng)時(shí)“文”和“言”不可能不走向一致,上古的《尚書》就是當(dāng)時(shí)的口語,但堅(jiān)持認(rèn)為修飾是必要的,雖不得不“隨西洋語言的習(xí)慣”,但也要“深通小學(xué)”。
從后來的實(shí)際情形來看,一批以魯迅為代表的白話文作家為白話的推行打下成功的基礎(chǔ),胡適“國(guó)語的文學(xué),文學(xué)的國(guó)語”設(shè)想得以實(shí)現(xiàn),章太炎“博考方言”的設(shè)想終成歷史,他對(duì)于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貢獻(xiàn)隱而不彰,逐漸為人所忽略。但他的貢獻(xiàn)卻并沒有被人遺忘。錢玄同也承認(rèn)受了老師的影響:“我得了古今一體,言文一致之說,便絕不敢輕視現(xiàn)在的白話,從此便種下了后來提倡白話之根。”胡適在1926年也坦陳中國(guó)語文的重要:“在這個(gè)我們的國(guó)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時(shí)候……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guó)語、漢字、語文這三樣?xùn)|西’來作聯(lián)絡(luò)整個(gè)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這三件其實(shí)只是‘用漢字寫國(guó)語的國(guó)語文’一件東西,這確是今日聯(lián)絡(luò)全國(guó)南北東西和海內(nèi)海外的中國(guó)民族的唯一工具。”劉師培在《<新方言>后序》指出了章太炎先生的苦心孤詣:“昔歐洲希,意諸國(guó)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fù)之勛,灌蕍于此。今諸華夷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而我們?cè)诮▏?guó)后,曾天真地幻想讓漢字走拉丁化的“改革”之路,以適應(yīng)全盤西化的文化岐途,結(jié)果怎么樣呢,相信歷史自會(huì)作出公正的評(píng)判。事實(shí)上,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一旦離開了漢字之根,必將如章太炎所預(yù)料的那樣,淪為游魂散魄,最后煙消云散。
章太炎的小學(xué)學(xué)問,雖有黃侃、陸宗達(dá)、王寧等傳人,但“為此這一學(xué)科所涉及的內(nèi)容,并沒有被后人接受,到五十年代后,竟至斷裂,幾成絕學(xué)。”但是他對(duì)中國(guó)語言文字保留倡導(dǎo)的功績(jī),我們實(shí)不能忘。
當(dāng)是時(shí),章太炎最深痛的就是對(duì)本國(guó)文化無自律自覺,逢迎隨波的行為,他深切明白“民族無自覺,即為他民族陵轢,無以自存”。他用一生的著述證明了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的“閎碩壯美之學(xué)”足以自信自立,不必尊崇遠(yuǎn)西之學(xué)。如今,我們的國(guó)學(xué)研究依舊要常常回味于章太炎,他所繼承構(gòu)建的中華文化傳統(tǒng),今日也亟待我們的重新發(fā)掘與建設(shè)。著名學(xué)者王富仁先生在《新國(guó)學(xué)論綱》中高度評(píng)價(jià)章太炎的國(guó)學(xué)成就:
我認(rèn)為,迄今為止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文化真正有實(shí)質(zhì)意義的發(fā)展,都是通過重新回歸傳統(tǒng)的形式具體表現(xiàn)出來的,而在西方文化直接影響下所取得的暫時(shí)的發(fā)展和變化,則往往帶有浮面的、虛矯的特征,一次次的文化回潮都會(huì)把這些發(fā)展的泡沫分流出去,而剩下的還是在這個(gè)過程中正統(tǒng)文化自身發(fā)生的那些微末的變化。正是因?yàn)槿绱耍绿纵^之與他同時(shí)代的康有為、梁?jiǎn)⒊?yán)復(fù)、王國(guó)維等人的學(xué)術(shù)研究在表現(xiàn)形式上更為“陳舊”,但在質(zhì)地上卻更為堅(jiān)實(shí)。
這段話說得入木三分。章太炎的學(xué)問博大精深,我自己曾師從陳旭鹿、湯志鈞、姜義華諸位先生注釋過他的著作,深感其國(guó)學(xué)情懷的博厚與淵明。但過去對(duì)他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往往批評(píng)為“復(fù)古”,現(xiàn)在看來未必呢!
二、梁?jiǎn)⒊墓诺淝閼?/strong>
梁?jiǎn)⒊?873-1929),在近現(xiàn)代政壇與文壇上,他的影響可以說超過了章太炎。章太炎早年一直依于梁?jiǎn)⒊髞矸值罁P(yáng)鑣,梁?jiǎn)⒊梁ジ锩霸谌毡緞?chuàng)辦《新民叢報(bào)》,宣傳改良,與章太炎主編的《民報(bào)》鼓吹革命展開論戰(zhàn)。梁?jiǎn)⒊c章太炎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也有很大不同,他主張?jiān)趥鞒袊?guó)學(xué)的基礎(chǔ)之上,大幅度地引進(jìn)西方的新學(xué),改革國(guó)民性,使中國(guó)真正走上現(xiàn)代化之路。梁?jiǎn)⒊砟暌餐顺稣氐綍S,成為清華國(guó)學(xué)院“四大導(dǎo)師”之首。不過,梁?jiǎn)⒊c章太炎晚年殊途同歸,離開政治,回歸學(xué)術(shù),這二人都表現(xiàn)出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特點(diǎn),即歷經(jīng)滄桑,學(xué)貫中西,充滿著國(guó)學(xué)情懷。
梁任公在百日維新中,大力宣傳維新變法的思想。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亡命日本,繼續(xù)宣傳他的新民說。他深有感觸地說:“求文明而從形質(zhì)入,如行死巷,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shì)必不能達(dá)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入精神,如導(dǎo)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御也。” 如何從精神改造入手,提高國(guó)人素質(zhì)呢?梁?jiǎn)⒊J(rèn)為,文學(xué)與藝術(shù)是一個(gè)重要的途徑,因此他倡導(dǎo)“小說革命”與“詩界革命”。
梁任公有一種深層的古典情懷,具體說來,便是對(duì)于古人的哀憫與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發(fā)表了兩次講演。在《屈原研究》的講演中,他以滿懷情感的講演向聽者介紹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來,深入淺出。他贊嘆:“中國(guó)文學(xué)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從前并不是沒有文學(xué),但沒有文學(xué)的專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傳詩歌之類,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們讀這類作品,頂多不過可以看出時(shí)代背景或時(shí)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現(xiàn)個(gè)性的作品,頭一位就是研究屈原。”梁任公充分肯定了屈原對(duì)于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從精神人格到藝術(shù)形態(tài)、審美風(fēng)格上的影響作用。最后他將屈原的作品與哥德相比較,贊嘆:“這類作品,讀起來,能令自然之美,和我們心靈相觸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學(xué)。”將學(xué)術(shù)與情懷相結(jié)合,這是國(guó)學(xué)大師的共同學(xué)術(shù)精神,非今日功利型的學(xué)術(shù)導(dǎo)向所可比擬。
在另一講《情圣杜甫》中,梁任公對(duì)于在中國(guó)過去被視為詩圣的杜甫,從新時(shí)代角度作了評(píng)判,提出:“第一,新事物固然可愛,老古董也不可輕輕抹煞。內(nèi)中藝術(shù)的古董,尤為有特殊價(jià)值。因?yàn)樗囆g(shù)是情感的表現(xiàn),情感是不受進(jìn)化法則支配的;不能說現(xiàn)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優(yōu)美,所以不能說現(xiàn)代人的藝術(shù)一定比古人進(jìn)步。第二,用文字表達(dá)出來的藝術(shù)——如詩詞歌劇小說等類,多少總含有幾分國(guó)民的性質(zhì)。因?yàn)楝F(xiàn)在人類語言未能統(tǒng)一,無論何國(guó)的作家,總須用本國(guó)語言文字做工具;這副工具操練得不純熟,縱然有很豐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為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我根據(jù)這兩種理由,希望現(xiàn)代研究文學(xué)的青年,對(duì)于本國(guó)二千年來的名家作品,著實(shí)費(fèi)一番工夫去賞會(huì)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梁?jiǎn)⒊瑥男屡f互動(dòng)的角度去分析前人,超越了當(dāng)時(shí)人的局限。
梁?jiǎn)⒊男≌f觀也明顯地貫徹了他的古典情懷。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中,十分重視小說作為一種通俗文學(xué)其中蘊(yùn)涵的社會(huì)心理,既肯定其中的積極意義,同時(shí)對(duì)其負(fù)面作用進(jìn)行了尖銳批評(píng):
今我國(guó)民輕棄信義,權(quán)謀詭詐,云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jī)心,舉國(guó)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guó)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綣戀床第,纏綿歌泣于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為一大事業(yè),兒女情多,風(fēng)云氣少,甚者為傷風(fēng)敗俗之行,毒遍社會(huì),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guó)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會(huì)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huì),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guó),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
梁?jiǎn)⒊J(rèn)為小說的教育作用與毒害作用同樣巨大,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有意識(shí)地將古典與現(xiàn)代人生相融合,以使傳統(tǒng)走向新生。
梁?jiǎn)⒊谥摹吨袊?guó)韻文里頭所表現(xiàn)的情感》一文中進(jìn)一步提出:“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它的本質(zhì)不能說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惡的方面,也有很丑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處亂碰亂迸,好起來好得可愛,壞起來也壞得可怕,所以古來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重情感的陶養(yǎng)。老實(shí)說,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將情感善的美的方面盡量發(fā)揮,把那惡的丑的方面逐漸壓伏淘汰下去。這種功夫做得一分,便是人類一分的進(jìn)步。”(《中國(guó)韻文里頭所表現(xiàn)的情感》)梁?jiǎn)⒊运┩ㄖ形魑幕膶W(xué)識(shí),在這段文章中概括了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中情感教育價(jià)值,他認(rèn)為對(duì)人的情感的培養(yǎng)有助于塑造新的國(guó)民人格。
梁?jiǎn)⒊撐乃嚂r(shí)還涉及情感教育中的審美趣味范疇。西方人喜歡談趣味無爭(zhēng)辨,而中國(guó)古代注重趣味與精神人格的融合。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藝觀中,有著豐厚的審美趣味學(xué)說,梁任公出于深厚的古典情懷,獨(dú)具只眼地看到了其中的現(xiàn)代人文價(jià)值。他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說:“趣味是生活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動(dòng)便跟著停止。好像機(jī)器房里沒有燃料,發(fā)不出蒸氣來,任憑你多大的機(jī)器,總要停擺。”他對(duì)趣味的理解,有點(diǎn)像王國(guó)維說的生活之欲,但王國(guó)維的生活之欲,是從叔本華哲學(xué)中推導(dǎo)出來的,帶有很大的悲觀色彩。梁氏論生活趣味則充滿著生活的樂趣,他認(rèn)為趣味本身就是生活的動(dòng)力,而不是生活痛苦的轉(zhuǎn)化,但他對(duì)人生的趣味是有褒貶的,有的趣味,如吃喝嫖賭這一類嗜好就是不好的。梁?jiǎn)⒊J(rèn)為,人的審美趣味的培養(yǎng)既要靠自己的先天器官,同時(shí)也依賴于后天的教育,即誘發(fā)的作用,而從事誘發(fā)的途徑不外乎三種,即文學(xué)、音樂與美術(shù)。梁?jiǎn)⒊瑢?duì)于美充滿著贊美之情,他說:
愛美本能,是我們?nèi)巳硕加械摹5杏X器官不常用或不會(huì)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個(gè)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沒趣的人;一個(gè)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沒趣的民族。美術(shù)的功能,在把這種麻木狀態(tài)恢復(fù)過來,令沒趣變?yōu)橛腥ぁ?rdquo;(《美術(shù)與生活》)
這可以說是一位國(guó)學(xué)大師人文情懷的彰顯。足以為我們的國(guó)學(xué)研究垂范示倫。
三、王國(guó)維的悲劇情懷
王國(guó)維(1877--1927),字靜安,清末秀才,號(hào)觀堂,在文學(xué)、美學(xué)、史學(xué)、哲學(xué)、古文字、考古學(xué)等各方面成就卓著,是近現(xiàn)代史上的最著名的學(xué)者之一。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被譽(yù)為“中國(guó)近三百年來學(xué)術(shù)的結(jié)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xué)術(shù)的開創(chuàng)者”。
王國(guó)維的學(xué)術(shù)歷程很獨(dú)特。他是先從接受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與美學(xué)出發(fā),然后再去從事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文史之學(xué)的,他的人文情懷,在其哲學(xué)與美學(xué)理論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所以在這里我主要從他的美學(xué)與文學(xué)理論談起。
王國(guó)維對(duì)人生的看法受中國(guó)古代的老莊、佛教與西方的叔本華、尼采哲學(xué)影響較深。由于特殊的人生經(jīng)歷,造成了王國(guó)維的悲劇人生觀,“欲與生活與痛苦,三者一而已矣。”欲望使人迷于自我而難于自撥,“蓋人心之動(dòng),無不束縛于一己之利害,獨(dú)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粹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論教育之宗旨》)他認(rèn)為美能夠凈化人生,使人從一己利害中擺脫出來。
王國(guó)維對(duì)美與自由的極力推崇,是與他對(duì)現(xiàn)實(shí)人生的極度失望有關(guān)的。他生活的清末民初中國(guó),整個(gè)社會(huì)被一種世紀(jì)末的情緒所困擾。王國(guó)維痛感于人們失去理想,惟知蠅營(yíng)狗茍,追逐實(shí)利,而這種心態(tài)又集中在濁臭不堪的官本位上。王國(guó)維以一個(gè)鐘情學(xué)問,追求真理的知識(shí)分子的良知,對(duì)這種濁污的社會(huì)機(jī)制與價(jià)值觀念猛烈加以抨擊:
吾中國(guó)下等社會(huì)之嗜好,集中于一利字,上中社會(huì)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為利之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會(huì)全體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難也。知拂之之不可,而忘夫獎(jiǎng)勵(lì)之之尤不可,此謂能見秋毫之末而不能見泰山者矣。(《教育小言十三則》)
王國(guó)維對(duì)中國(guó)歷史上以官獎(jiǎng)勵(lì)學(xué)問與職業(yè)的做法深為不滿,認(rèn)為以官獎(jiǎng)勵(lì)學(xué)問的結(jié)果便是“剿滅學(xué)問也”,勢(shì)必造成道德衰頹,社會(huì)上都將做官作為人生的最大嗜好,“夫至道德、學(xué)問、實(shí)業(yè)等皆無價(jià)值,而惟官有價(jià)值,則國(guó)勢(shì)之危險(xiǎn)何如矣!社會(huì)之趨勢(shì)既已如此,就令政府以全力補(bǔ)救之猶恐不及,況復(fù)益其薪而推其波乎!”(《教育小言十三則》)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長(zhǎng)時(shí),也對(duì)社會(huì)上彌漫的濁污蒸臭的官本位深惡痛絕,號(hào)召學(xué)生要潛心學(xué)問,大學(xué)就是培養(yǎng)做學(xué)問的人,而不是讀書做官,求利謀財(cái),扭曲人格。王國(guó)維從這種角度出發(fā),將美學(xué)問題與改造國(guó)民人格的問題結(jié)合了起來,表現(xiàn)了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一以貫之的憂思精神。
近代以來,一些愛國(guó)人士對(duì)鴉片禍害中國(guó)人的現(xiàn)狀痛心疾首,林則徐更是采用嚴(yán)厲的行政措施來禁毒,但是并未產(chǎn)生根本的效用。王國(guó)維在《去毒篇》中認(rèn)為,鴉片在社會(huì)上的肆虐,從心理學(xué)來說,則是人們情感上的失去寄托與慰藉。尤其對(duì)于中國(guó)人來說,沒有西方人與印度人的宗教作為精神家園,而以入世的態(tài)度來對(duì)待周圍世界,王國(guó)維在《紅樓夢(mèng)評(píng)論》中就對(duì)中國(guó)人的這種樂天精神與圓滑態(tài)度深有研究與感嘆。他認(rèn)為,美學(xué)作為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橋梁,最適應(yīng)中國(guó)人的情感世界:“我國(guó)人對(duì)文學(xué)之趣味如此,則于何處得其精神之慰籍乎?求之于宗教歟?則我國(guó)無固有之宗教,印度佛教已久失之生氣。求之于美術(shù)歟?美術(shù)之匱乏,亦未有如我中國(guó)者也。則夫蚩蚩之氓,除飲食男女外,非雅片賭博之歸而奚歸乎?”(《教育偶感四則》)他通過比較中國(guó)的精神文化不同于西方和印度的特點(diǎn),認(rèn)為國(guó)人嗜食鴉片有其必然性。從而喚起人們對(duì)中國(guó)人精神世界問題的關(guān)注,表現(xiàn)出憂國(guó)憂民的情懷。
王國(guó)維認(rèn)為要使中國(guó)人的感情世界得到拯救,主要是使感情有一個(gè)得到棲養(yǎng)的園地。他認(rèn)為一個(gè)重要途徑就是美術(shù)。美術(shù)通過藝術(shù)的方式來陶冶人的情趣,使人的情感得到升華,得到寄托,而這方面中國(guó)是很欠缺的,惟其欠缺,才需要大力提倡。另一個(gè)是對(duì)宗教問題的重新思索。在這個(gè)問題上,王國(guó)維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認(rèn)為宗教并不適合中國(guó),中國(guó)人沒有固定的宗教,印度佛教在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衰退。但對(duì)于一般的勞苦大眾來說,他們終歲辛苦,又沒有受教育的機(jī)會(huì),得不到什么人生的樂趣,要使他們得到一絲安慰,只有宗教的慰藉:“幸而有宗教家者教之以上帝之存在,靈魂之不滅,使知暗黑局促之生活外,尚有光明永久之生活。”總而言之,“有”聊勝于“無”,對(duì)于普通百姓來說,有精神上的寄托總比沒有要好。在這一點(diǎn)上,他的學(xué)說顯然與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有所不同。但王國(guó)維將宗教和美育與當(dāng)時(shí)對(duì)國(guó)人靈魂的挽救相融合,與構(gòu)建人格相結(jié)合,這種思路不乏悲天憫人的情懷。
王國(guó)維指出,人的心理活動(dòng)源于生活之欲。當(dāng)衣食住行這些基本的東西滿足之后,就會(huì)產(chǎn)生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如娛樂、游戲與消遣等欲望沖動(dòng)。德國(guó)哲學(xué)家與美學(xué)家席勒認(rèn)為人的游戲是“物質(zhì)沖動(dòng)”與“形式?jīng)_動(dòng)”所組成的,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之中,物質(zhì)沖動(dòng)總囿于功利的需要,近乎于謀生的勞動(dòng),而形式?jīng)_動(dòng)則是完全流于外在的做作,惟有在審美之中,實(shí)在與形式,即感性與理性得到了統(tǒng)一。王國(guó)維也認(rèn)為,無論是小孩的游戲,還是大人的游戲,都是人的剩余精力的發(fā)泄,是生存欲念的轉(zhuǎn)化,其表現(xiàn)形式有各種各樣,比如博奕、煙酒,以及文學(xué)與戲曲等等,文學(xué)活動(dòng)與這些游戲就宣發(fā)欲念,升華人的嗜好來說,并無不同之處,“文學(xué)者,游戲的事業(yè)也。人之勢(shì)力用于生存競(jìng)爭(zhēng)而有余,于是發(fā)而為游戲。婉孌之兒,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無所謂爭(zhēng)存之事也。其勢(shì)力無所發(fā)泄,于是作種種之游戲。逮爭(zhēng)存之事亟,而游戲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勢(shì)力獨(dú)優(yōu),而又不必以生事為急者,然后終身得保其游戲之性質(zhì)。而成人之后,又不能以小兒之游戲?yàn)闈M足,于是對(duì)其自己之感情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詠嘆之,以發(fā)泄所儲(chǔ)蓄之勢(shì)力。”(《文學(xué)小言》)王國(guó)維借鑒西方的美學(xué)學(xué)說,站在人類生存學(xué)的角度,對(duì)人的審美形成作出了深刻的分析。這些學(xué)說盡管在西方那兒早已不是新理論,但是王國(guó)維用它來解析中國(guó)的心理危機(jī)與國(guó)民素質(zhì)低下的問題,得出了同時(shí)代人未曾得出的深刻結(jié)論。
王國(guó)維將傳統(tǒng)文化中老莊思想與西方康德、叔本華、尼采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力圖建設(shè)成具有中國(guó)特點(diǎn)的思想體系。由于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離他的理想太遙遠(yuǎn),王國(guó)維于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故陳寅恪寫下了著名的《清華大學(xué)王觀堂先生紀(jì)念碑銘》:
士之讀書治學(xué),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yáng)。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dú)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jié),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shí)而不章。先生之學(xué)說,或有時(shí)而可商。惟此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可以說是對(duì)于中國(guó)古代知識(shí)分子人生境界與學(xué)術(shù)精神相統(tǒng)一的表征,其中所揭示的“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jīng)成為士人人格精神的座右銘。
四、陳寅恪的守望情結(jié)
陳寅恪,我國(guó)20世紀(jì)的國(guó)學(xué)大師,他的人生本身也是中國(guó)文化的象征,堪稱一段傳奇。他是一位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的忠實(shí)守望者,他留下的著述,只是平生廣博學(xué)說的冰山一角,但他的精神人格留下的寶貴無形遺產(chǎn),已全部凝聚成他墓碑上的“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堪稱先生盡一生心血譜寫的絕唱。
王國(guó)維生前與陳寅恪即為“許我忘年為氣類”的相知,二人在動(dòng)蕩時(shí)局之下,都對(duì)傳統(tǒng)文化肩負(fù)著沉重使命感與憂患意識(shí),并為其衰亡深深感到苦痛。1927年6月,王國(guó)維在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后,在昆明湖魚藻軒旁縱身投湖。他身后各種揣測(cè)紛起,在與王國(guó)維心靈相知的陳寅恪看來,這些皆為“流俗恩怨榮辱萎縮齷齪之說”,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替亡者宣告:“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shí),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dá)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說明“先生以一死見其獨(dú)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性之興亡。”王國(guó)維并非單純殉于某個(gè)朝代、一家一姓,而是殉于傳統(tǒng)文化的衰亡:“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shù)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這苦痛的道白是為王國(guó)維而發(fā),但又何嘗不是出于陳寅恪的內(nèi)心獨(dú)白。因?yàn)殛愐〉脑忈專鯂?guó)維之死得到了升華,其精神人格超越而得到了永生。王國(guó)維的死亡也給了陳寅恪巨大的震動(dòng)和一生的影響,王國(guó)維沒有完成的事業(yè)要留給他去繼續(xù)完成,這歷史個(gè)人帶來的悲壯的使命意識(shí)使陳寅恪不禁“謬承遺命傷神”,這種自覺也促使他一生歷經(jīng)苦辛而終不改其志向。即使在政治氣氛非常緊張的五十年代,面對(duì)北京向他的召喚,陳寅恪在《對(duì)科學(xué)院的回復(fù)》中仍說:“獨(dú)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zhēng)的,且須以生死力爭(zhēng)……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陳寅恪確實(shí)是用一生的時(shí)間去孤獨(dú)地實(shí)踐著獨(dú)立自由精神的實(shí)現(xiàn)。
雖然追求科學(xué)真理之獨(dú)立、自由之觀念來自于近代西方,但陳寅恪這種畢生追求的信念實(shí)與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孔孟所云“士,志于道”何為相似。這種古典儒家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jiān)毅決絕,注定地造就了陳寅恪的悲劇人格。他出身名門,繼承了祖父陳寶箴與父親陳三立的家門學(xué)風(fēng),終身保持著名門士族的傲骨與清高。好友吳宓曾評(píng)價(jià)“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中國(guó)近世之模范人家……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fēng),學(xué)問識(shí)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绔之習(xí),所謂‘文化之貴族’。”這種文化貴族的孤傲倔強(qiáng)心態(tài)使他更加不愿向政治權(quán)威屈服,但也體會(huì)到更深的痛苦。早年流離中丟失了彌足珍貴的書稿資料,致使他計(jì)劃中的許多書未能見世人,顛沛流離的歲月毀壞了他的健康,更在創(chuàng)作力最旺盛的中年奪走了他的雙目,晚年更遭遇臏足之苦,同時(shí)忍受著極大的羞辱與折磨。這一切都注定了他早期宏偉的學(xué)術(shù)理想難以得到實(shí)現(xiàn),屬命河汾的強(qiáng)烈愿望與殘酷的現(xiàn)實(shí)在煎熬著他,他悲涼的生命情調(diào)浸染在詩歌中,留下了大量帶有“淚”、“傷”等字眼的血淚詩句。像王國(guó)維那樣選擇高貴的死去也許比繼續(xù)艱難生存要容易得多,但弘揚(yáng)獨(dú)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強(qiáng)烈生命意識(shí)促使他堅(jiān)持在黑暗中鉤沉索隱,以口述而完成了經(jīng)典巨著《柳如是別傳》。
王國(guó)維的死和陳寅恪的生都是一種深沉的文化選擇,帶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強(qiáng)烈使命感,與類似司馬遷那樣忍辱偷生發(fā)憤著書、藏之名山留待后人的堅(jiān)強(qiáng)愿望,陳寅恪在晚年將生命之火全力點(diǎn)燃,丹青難寫是精神,他用傳統(tǒng)士人的堅(jiān)貞完成了他最后的工作,有如《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所說,他“為后世學(xué)人提供了一種在文化苦戀及極濃的憂患意識(shí)煎熬下生命長(zhǎng)青的典范”。
生活狀態(tài)在于自己的選擇,學(xué)人可以選擇與當(dāng)權(quán)者合作,追求名利雙收,也可以固執(zhí)地堅(jiān)持理想,痛苦或者毀滅。陳寅恪在對(duì)歷史的考索中,意識(shí)到“值此道德標(biāo)準(zhǔn)社會(huì)風(fēng)習(xí)紛亂變易之時(shí),此轉(zhuǎn)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jí)之人,有賢不肖巧拙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陳寅恪選擇做賢者拙者,生死力爭(zhēng)獨(dú)立與自由,堅(jiān)決使學(xué)統(tǒng)獨(dú)立于政統(tǒng)之外,不惜做時(shí)代邊緣的孤獨(dú)者。他拒絕登上國(guó)民黨的飛機(jī)前往臺(tái)灣,在五十年代向“毛公”、“劉公”提出驚世駭俗的請(qǐng)求,“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xué)習(xí)政治。”在他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雖痛惜自己未能完成年少時(shí)的宏愿,但“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xué)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他終其一生實(shí)踐了他寫在王國(guó)維紀(jì)念碑銘上的宗旨。
在“晚年唯剩頌紅妝”與“聊作無益之世,以遣有涯之生”的自嘲中,陳寅恪將晚年的光陰都傾注在陳端生與柳如是這兩位女子身上。聽說過陳端生之名者甚為寥寥,其《再生緣》于常人看來也就是平庸的才子佳人小說,而身為“秦淮八艷”的柳如是一向受正統(tǒng)文人鄙薄。一代治史大師,選擇如此“非主流”的研究對(duì)象,必有深意存焉。因?yàn)檫@兩位女子與陳寅恪本人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堅(jiān)持獨(dú)立自由的靈魂,而不為世人所容。陳寅恪不忍見到這樣的奇女子終究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他就是要為歷史上不受重視甚至屢受譏謗的弱女子“正名”樹傳,來譜寫自己獨(dú)立精神、自由意志之心曲。
陳寅恪贊美因作者的獨(dú)立精神而帶給《再生緣》的優(yōu)美文字,“《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dú)勝者,實(shí)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yùn)用其對(duì)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xué),舉此一例,可概其余。”從《再生緣》主人公孟麗君的身上,陳寅恪“則知端生心中于吾國(guó)當(dāng)口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二綱,皆欲藉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dú)立之思想,在當(dāng)日及其后百余年問,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讀出了陳端生挑戰(zhàn)傳統(tǒng)倫理綱常的非凡勇氣;而研究柳如是,陳寅恪“披尋錢柳之篇什于殘闕毀禁之余,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fā)自當(dāng)日之士大夫,猶應(yīng)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于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dāng)時(shí)迂腐者所深低,后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柳如是雖身為妓女,但歷經(jīng)磨難而始終堅(jiān)守民族氣節(jié)和文化操守,卻深為流俗所傷,陳寅恪認(rèn)為其光輝人格不亞于屈原等士大夫,將其引為異代知己,稱柳如是為“罕見之獨(dú)立女子”。
正如學(xué)者陳明所說,飽受身心折磨的晚年陳寅恪,“既要維持文化擔(dān)待,又要安頓生命情懷,柳如是,一個(gè)有文化操守的弱者,自是他唯一可能的選擇”。在孤寂黑暗的世界中,陳寅恪“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duì)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創(chuàng)造了以心靈情感來研究歷史、文史合一的經(jīng)典之作。在困居一室的精神遨游神交中,陳寅恪也超越了苦難,對(duì)自己的境遇釋然開懷:“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shí)一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淹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
身為學(xué)院派的研究學(xué)者,陳寅恪對(duì)中國(guó)的文化建設(shè)和人才培養(yǎng)傾注了大量心血。如何在獨(dú)立、自由的環(huán)境下培育出擁有獨(dú)立自由人格、并足以承擔(dān)弘揚(yáng)本國(guó)文化的人才,是他念念不忘的大事。在1931年清華大學(xué)建校20周年的講話《吾國(guó)學(xué)術(shù)之現(xiàn)狀及清華之職責(zé)》中,他開篇就強(qiáng)調(diào):“吾國(guó)大學(xué)之職責(zé),在求本國(guó)學(xué)術(shù)之獨(dú)立。”認(rèn)為“士之讀書治學(xué),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這“俗諦”便是政治,起初是三民主義,而后是馬克思主義,學(xué)術(shù)之根本在于求真,而這在中國(guó)歷史上卻是經(jīng)幾代學(xué)人的抗?fàn)幉沤K究被認(rèn)可的。陳寅恪“論學(xué)論治,迥異時(shí)流”,疾呼“國(guó)可亡,而史不可滅”,認(rèn)為這是“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他忠告“救國(guó)經(jīng)世,尤必以精神之學(xué)問(謂形而上之學(xué))為根基”,擔(dān)心將來中國(guó)“專謀以功利機(jī)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shì)必至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將這些話放于現(xiàn)今,更能凸顯陳寅恪的遠(yuǎn)見卓識(shí)。
按照陳寅恪的標(biāo)準(zhǔn),現(xiàn)今大學(xué)教育仍然注重培養(yǎng)技術(shù)人才,人文精神教育培養(yǎng)缺失,已經(jīng)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huì)問題。在陳寅恪看來,人文精神的陶冶和民族學(xué)術(shù)的繼承發(fā)展是文化教育最重要之事。他對(duì)于中華文化懷著堅(jiān)定的希望,在當(dāng)年“全盤西化”如火如荼之時(shí),他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jìn),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振復(fù)。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zhǎng),及至盛夏,枝葉撫疏,亭亭如車蓋,又可以庇蔭百十年人矣。”只要我國(guó)文化“本根未死”,春風(fēng)回暖之日必會(huì)復(fù)興重振。一味吸收西方文化,必將亡本國(guó)之文化,比亡國(guó)更為慘痛。他在為馮友蘭的《中國(guó)哲學(xué)史》(下冊(cè))撰寫審查報(bào)告時(shí)說得明白:“竊疑中國(guó)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shí)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jié)局當(dāng)亦等于玄奘唯識(shí)之學(xué),在吾國(guó)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xué)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獨(dú)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即為陳寅恪繼承傳統(tǒng)文化之精髓而又熔鑄西方近代思想,著眼于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而提出的,唯有此學(xué)貫中西的大家,才能清醒地看到保持本國(guó)學(xué)術(shù)獨(dú)立的同時(shí)吸收西方文化,才能使本國(guó)文化昌盛不衰。先生的遺志,此刻正擔(dān)負(fù)在我輩肩頭。陳寅恪先生之學(xué)不必人人皆學(xué),但“惟此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值得每個(gè)中國(guó)學(xué)人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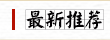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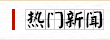

 浙公網(wǎng)安備 33102402000349號(hào)
浙公網(wǎng)安備 33102402000349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