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審美世界的國學
來源:中國網 作者:袁濟喜 時間:2015年07月08日 人參與 評論 0 條 我要評論
原標題:《國學十講》第五講:走向審美世界的國學
在這一講中,我們接著第四講《國學與詩興精神》的內容,繼續就國學與審美世界問題進行討論。如果我們將國學當作中華文化的精髓,便不得不承認,它具有形而上的人生境界與形而下的器用的結合,而審美與文藝境界,則是這種形而上人生境界的凝聚。中國文化關心人生問題,充滿世俗情味,但是又不滯泥于塵俗,而是追求更高的境界,由此而決定了中國文化不依賴于宗教的救贖,也能達到人生的超越與精神的皈依,建設自己的精神家園。所以,國學的境界往往存在于審美世界與文藝境界之中。要了解中華文化之神韻,必然要討論它的最高層次,也就是審美與人生的關系問題,所以在這一講中,我們就此話題展開論述。
一、審美與人生問題
中國文化善于將人生審美化。中國號稱禮義之邦,在很早的商周時代,就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禮樂文明。南宋理學家朱熹說:“三代之時,禮樂用于朝廷,而下達于閭巷。”(《答陳體仁》)從禮樂的功能來說,禮以別異,樂以合樂,共同組成中華文明的體系和秩序。中華民族因為有了禮樂文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世界各國的贊嘆,是國學的標志所在。
中國古代社會用禮樂來美化人生,建立和諧之治,沒有禮樂作為基礎,和諧社會便無從談起。我們不能設想,一個沒有起碼禮樂教養的社會,會成為和諧理想的世界。當代美學家宗白華先生在《藝術與中國社會》中指出:“禮和樂是中國社會的兩大柱石。‘禮’構成社會生活里的秩序條理。禮好象畫上的線文鉤出事物的形象輪廓,使萬象昭然有序。孔子曰:‘繪事后素’。‘樂’涵潤著群體內心的和諧與團結力。”宗先生強調中國古代文化以審美與藝術化為旨趣,這是卓有識見的。禮樂的最后根據,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禮記》上說:“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中國古老的禮樂文化,直接秉承農業社會人們的自然觀與社會觀,具備了審美的價值。既然天地以和為美,那么人類社會的禮樂也是秉承天地之和而產生的,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便是這種觀念的反映。中國最早體現在禮器與玉器,以及禮樂文化中的美學觀念,具有將人倫與天地相貫通的精神蘊涵,小小的玉器與禮器,不僅是裝飾與把玩之物,更主要的是由小見大,映射出先民們追求禮樂與天地同和的審美觀,具有本體論的價值。

孔子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傳統禮樂進一步分化與重組,人們開始將詩歌從音樂、舞蹈分離出來,同時又注重其中的內在聯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贊揚孔子整理《詩經》時的貢獻時指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可見孔子非常重視《詩經》與禮樂既相結合,又相獨立,以發揮各自不同的效用。孔子強調詩歌與音樂具有陶冶性情之功能,以美化人生,培養人格。孔子認為,所謂人格,首先意味著人性的自我超越,他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明確地在這里將道德的境界分為三個層次,即一般知曉,開始喜歡,樂以為之三個層面。孔子曾贊揚其大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孔子贊美顏回的賢達高亮,在于顏回的道德境界已經超越了一般外在約束,而趨于內心的自我滿足,而此種自滿足,接近于宗教體驗與獻身境界,它與審美中達到的心理愉悅是相通的。現代新儒學欣賞的孔顏人格,實質上即是這種審美人格境界。孔子在談到自己的人生境界時也曾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所謂“樂亦在其中矣”,是人在弘道揚義過程中形成的自我尊嚴感,也是一種審美人生境界。
在《論語·先進》中著名的“子路、曾皙、公西華侍坐”一章中,孔子曾與他的學生討論過人生理想: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 :“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 :“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孔子在與其弟子探討人生志向時,雖對子路、冉求等人出將為相的志向有所嘉許,但是他最欣賞的還是曾點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那種超越世態的審美化的人生方式。

莊子
中國文化,既受儒家的影響,同時受道家一派的影響更深,這是因為儒家重在社會人事的建樹,追求內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對于人類學本體論上的關注遠不如道家,而美學恰恰是對于人類終極意義的尋繹,是對于人生自由的陶醉,這一點與道家思想的境界不期而遇,殊途同歸。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說過:“中國人的特性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來自道家的傳統。中國如果沒有道家,就像大樹沒有根一樣。”李約瑟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看到了道家思想深入心靈的魅力所在。中國偉大的文藝家大都與老莊思想有著深刻的淵源關系,這并不是偶然的。莊子所說的道,含有人格化的縮影,帶有明顯的審美自由的意蘊。《莊子·知北游》中說: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莊子心目中的道乃是天地之大美。莊子認為,自然界的純美與可貴,就在于一切都是天造地設的,“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駢拇》),野鴨的腿雖短,但接上一截則長;鶴腿雖長,但裁去一段則悲。莊子以此來說明人類切勿做一些毀壞自然的蠢事。如果說,莊子認為最好的人生教育就是啟示人們自己去發現美,這美并不遙遠,并不玄秘,就在于那天蒼蒼,野茫茫,云行雨施的大自然之中,而人一旦來到自然的懷抱中,就會處于身心自由與解放的境地。莊子曾將他的理想人格分成圣人,神人,真人,至人,德人,天人,全人等等,其大要是對于世俗的超越,與審美精神相通,這一點與老子理想人格重智慧思辨的特點不同。
為了給自己的人格精神罩上美麗的光彩,莊子以浪漫絢麗的筆觸,描寫了這些形象,《逍遙游》中描繪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在莊子書中,這些描寫還很多。莊子的文學精神與人生超越在這些文字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這就是理想人格由于具有超凡入圣的功能,精神高尚,于是沒有了塵世之累。
莊子的人格理想在魏晉風度中得到彰顯。比如魏晉名士嵇康所向往的也是一種審美化的人生,它的針對性是非常明確的。嵇康認為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在現實中是無從實現的,當時是一個人人奔競的時代,漢末以來,社會動亂,傳統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念受到沖擊,而新的人生觀念尚未成為社會共有的價值體系,因而人心的浮蕩,道德的崩潰,造成了社會風氣的虛靡,而司馬氏的所謂“以孝治天下”更使社會處于人人作假的環境之中。嵇康無力去改造這樣的社會,只好在自己的人生追求中求得心靈的和諧與愉快,為此他倡導《養生論》。“養生論”并不是從生理上的長壽去說的,而是指抗拒外界的物質誘惑,保持純潔之心靈,這種心境是人格獨立的前提,“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嵇康發揮了老莊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的人生哲學,倡導知識分子的潔身自好、抗拒濁流。在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他在嚴詞拒絕山濤薦他代替自己任吏部員外郎一職時,自敘人生志向:“今但愿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灑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嵇康在當時世人奔競成風,官場濁穢時,以養生之術堅守自己的人格操行,同時又在藝術美的境界中獲得人性的滿足,因為在藝術美的境界中,人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追求可以獲得超升,可以擺脫外界的困擾。嵇康在他的四言詩中,寫下了不少“琴詩自樂,遠游可珍”的詩,其中有一首著名的《贈秀才入軍》的詩,可以視為嵇康人格境界與藝術境界的天合: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流磻平皋,垂綸長川。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詩中借寫哥哥嵇喜赴軍途中游歷山水的情景,實際上是寫嵇康想象在山水自然之中陶冶身心,琴詩自樂的情景,特別是詩中“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四句詩,將詩人在彈琴觀景時與物合一,在審美的自由境界中獲得人格解放的情形寫得至真至美。正像《晉書·嵇康傳》所說,“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他的人生態度直接影響到晉宋時期的陶淵明的人生與文學。
當然,中國傳統美學雖然存在著儒道兩家的對立,但是這兩派的觀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互相補充的。儒家“與天地參”的道德境界,與道家的自然之道也可以相通,孔子晚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浴沂舞雩”的美境中獲得解脫,他的“浴沂舞雩”與莊子的“逍遙游”是相通的。儒道兩家人格的不同有助于中國文化的活力與人生境界的多元化,他們彼此之間的互補,造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的廣博精深,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受儒學熏陶的文化人物,沒有不出入佛老的。蘇軾、王夫之等人就是典型。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正是在儒道與多家文化的沖突與互補中顯示出來的。沖突與對立造就了傳統文化的活力與生氣,而互補則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懷。
二、中國文化凝聚于審美境界之中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人格境界構成文藝審美境界的底蘊,這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論及境界時也主要是從這方面去立論的。他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然滄浪(嚴羽)所謂興趣,阮亭(王士禎)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王國維在這里強調境界的特點是“自成高格”,認為嚴羽與王士禎等人的“興趣說”與“神韻說”不如他的“境界論”更能說明詩詞的精髓所在。王國維論詩詞推舉的是一種高尚的風韻與格調,是作者心靈世界的升華。中國文化即國學的主體,最高的境界在于人生的超越與人格的完善,中國文化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審美型的文化。宗白華先生曾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中提出:“就中國藝術方面----這中國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貢獻的一方面---研尋其意境的特構,以窺探中國心靈的幽情壯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他提出從意境可以直窺中國人的心靈奧秘,值得我們深思。

嵇康
中國有著豐富的美學歷史資源,是國學的重要部分。藝品出于人品,藝品貴在含蓄蘊藉、回味無窮,這是中國美學的基本觀念。意境是藝術到達很高層次后的產物,它體現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審美心態,即講究味外之旨。中國古代美學往往將審美稱作為“味”,但是最高的審美境界卻是超越感官的精神之域,在這片精神之域中,有無上的意義可以品味與追尋,是人文精神的結晶。老莊論及審美時,總是將美與超形質的精神相貫通。老子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老子·三十五章》)魏晉玄學家王弼的《老子注》中對此解釋道:“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也就是說,道是無聲無味的,常人往往為美味美聲所吸引,而道則是超越形質,不為世人所好的,而恰恰是這種超越形質的道,能夠使人的精神為之受用與陶醉。世俗之人往往將味視為生理快感,如孟子說:“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老子則認為“道”較之這種味道,是一種更高形態的精神品味。王弼曾經說過:“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老子注》)他認為“道”雖然無形無狀,但是惟其如此,可以包容一切,涵蓋一切,是萬事萬物的精神實體,它能夠穿透人們的審美空間,引起主體的無限性的想象與發揮。嵇康在談到最高的音樂境界時也指出:“夫唯無主于喜怒,無主于哀樂,故歡戚俱見。”(《聲無哀樂論》)嵇康提出音樂中的境界越是超妙難識,就越是能夠引發不同的人們的心理反應,產生奇妙的審美效果,他們的理論是中國古代意境理論的哲學前提。唐代末年的詩論家司空圖吸取了老莊哲學與魏晉玄學的理論滋養,提出精神實體的“道”乃是美的本原。《二十四詩品》的首品《雄渾》將這種美學觀形象而生動地表現出來: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
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
荒荒油云,寥寥長風。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所謂“大用”指宇宙的本體“道”,“大用外腓”也就是說道外現于具體事物中,而其“真體”,即內在的本體“道”卻是唯一真實的存在。“荒荒油云,寥寥長風”之類的自然美景,都是由“道”派生出來的。司空圖的這一觀點,猶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美學》中所說,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中國美學將藝術美感與生理之味結合起來,認為精神之味較之生理快感更為高級,強調美感是不同于動物快感的精神享受,這種美學觀是很有價值的,在今日中國生理愉悅涵蓋藝術美感的情況下,值得我們深思。

顧愷之《洛神賦》
書法意境理論也是隨著漢魏以來儒學的衰落與玄學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書法與繪畫相比,其象征與抽象的特點更為明顯,因而在表達意蘊與抒發情感方面具有更加廣闊的天地,它雖然從自然中汲取營養,但是在心靈的創造與意境的營造方面要求更高。漢魏時代的書法理論家認為書法是與《周易》相同的用形象來表達天地之意的產物,它經過書家的創造而顯示出不同的風采。東漢的崔瑗與蔡邕等人就說過書法之形與天地萬物的對應關系,其中意蘊千變萬化,不可窮盡。迄至魏晉時代,一些書法理論著重用言意理論來說明書法美學的一些問題。比如成公綏《隸書體》論隸書時說:“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隸書雖以端凝方正為特點,但其中也要傳達出意蘊。至于草書,更是講究意的神巧。如索靖《草書勢》云:“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滋生。”他強調草書要善于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意境。魏晉書論家看到了書法藝術較之繪畫藝術來說,是一種更為抽象與玄奧的線條藝術,因此,書法之妙是一般的人難以知曉的,需要沿波討源、由表及里的欣賞。鑒賞之難,在于不能達其意境。
東晉書論家衛恒在《四體書勢》中則強調:“賭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論,不可勝原。研、桑不能計,宰、賜不能言。”衛恒認為書法之妙是難以盡說,不可勝計的。東晉書法泰斗王羲之在與友人的書信中也言及書法之妙在于意內形外,蘊含無窮,“頃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法書要錄》)王羲之認為書法是用來傳達作者審美意蘊的,而這種意境是言說不盡的。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說:“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跡。若精意玄鑒,則物無遺照。”(《法書要錄》)古代書論家論書法的玄奧的話,頗令我們想起德國文學家歌德論“精靈”的話:“精靈在詩里到處顯現,特別是在無意識狀態之中,這時一切知解力和理性都失去了作用,因此它超越一切概念而起作用。”歌德用“精靈”來說明詩中的意蘊與靈感現象,其實,除去其中的神秘成分,歌德所說的“精靈”是指詩中隱含的意蘊與境界,它在書法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
書論中的意境學說,說明了中國書法中的靈魂在于其心靈的創造力,鄧以蟄先生在《書法之欣賞》指出:“吾國書法不獨為美術之一種,而且為純美術,為藝術之最高境。何者?美術不外兩種:一為工藝美術,所謂裝飾是也;一為純粹美術。純粹美術者,完全出諸性靈之自由表現之美術也,若書畫屬之矣。”沈尹默先生在《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中贊嘆:“世人公認中國書法是最高藝術,就是因為它能顯出驚人奇跡,無色而具畫圖的燦爛,無聲而有音樂的和諧,引人欣賞,心暢神怡。”這些近代著名書法理論家的論述都指出了書法之妙在于其意境的靈動與精神的創造,由于意境的創造,使得書法能夠以高度傳神寫意的形式之美體現出藝術美的特質。書法美肇自于天地自然,然而經過心靈的再創造,形成了特殊的意境之美,因而其陶冶心靈的魅力是其他藝術所不具備的。詩是以文字語言符號來表現性靈與精神的,它事先已經被文字符號所整理,而書法直接以非語言符號的線條來傳達出人的情性,其意境更具純粹美的意蘊。
中國藝術之意境是中華民族心靈與人格的凝聚。它受屈原與莊子的影響很深,體現出中國古代文藝中的人格互補。宗白華先生曾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中提出:“所以中國藝術意境的創成,既須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曠空靈。纏綿悱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萬物的核心,所謂‘得其環中’。超曠空靈,才能如鏡中花,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這不但是盛唐人的詩境,也是宋元人的畫境。”宗先生提出了中國藝術的境界從文化淵源來說,是莊子精神、屈原情感和佛教禪境的融合。從美學范疇來說,意境觀念是從先秦意象觀念演變而來的,意象之說來自于先秦《周易》與莊子的言意之辨,但是這種美學范疇終究停留在藝術形象的范疇,未能進入到藝術心靈的深入,惟有六朝佛教境界說的進入中國文化領域,人們才用它來說明藝術的最高層次是心靈的攀援與意識的空靈,最能表征審美境界的超越功利性,使宇宙與自我合于內在的無際之境,不隔之境。中國美學后期的圓通,顯然與佛教思想的提升分不開的。南宋嚴羽的以禪喻詩更是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佛教禪宗的思想不可能消解掉中國文化的世俗精神,從某種意義來說,是使中國人的世俗精神獲得了形而上之超越態度與品味。李澤厚先生在《華夏美學》中論及禪宗對中國審美心理的升化作用時指出:“中國傳統的心理本體隨著禪的加入而更深沉了。禪使儒、道、屈的人際——生命-——情感更加哲理化了。既然‘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更何夕,其此燈燭光’(杜甫詩),那么,就請珍惜這片刻的歡娛吧,珍惜這短暫卻可永恒的人間情愛吧!如果說,西方因基督教的背景使無目的卻仍有目的性,即它指向和歸依于人格神的上帝,那么在這里,無目的性自身便似乎即是目的,即它只在豐富這人類心理的情感本體,也就是說,心理情感本體即是目的。它就是最后的實在。這,不正是把人性自覺的儒家仁學傳統的高一級的形而上學化么?它不用宇宙論,不必‘天人同構’,甚至也不必‘逍遙游’,就在這‘驀然回首’中接近本體而永恒不朽了。”李澤厚先生的論述,大略地指出了禪宗與佛教對于中國人心靈世界與文藝境界的作用,近代以來,中國美學重要人物,如豐子愷、王國維、宗白華、李叔同、蔡元培等人都受到過佛教思想的影響,這并不是偶然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淵遠流長,生生不息,決定了它雖然經歷了外來文化的沖擊,也依然能夠傳承下來,而不會走向衰亡。中國傳統美學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固然有許多消極的一面,但是傳統文化中的對民族與人類命運的關注,對真善美價值的不懈追求,卻是與現代啟蒙精神有相通之處,是人類文明的精萃,是可以通過改造與現代性互相發明的。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許多有志之士痛感于國力的衰弱,國民的愚昧,繼承了傳統士大夫的憂患意識,大聲疾呼,倡言立論,鮮明地將美學與增進國民之道德相結合。近代美學的主要精神,就是將立人為本與傳統文化中憂患意識相結合。涌現出一批學貫中西,融會古今的美學家。這些美學家同時也是國學的重要人物,例如梁啟超與王國維等人,他們寫過《人間詞話》、《情圣杜甫》等重要的美學論著,說明走向審美世界的近代國學,充滿著人文關懷的情味,在今天仍然為我們所鐘愛與傳承。

- 上一篇:國學與詩興精神
- 下一篇:從北京奧運看國學的普世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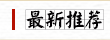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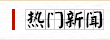

 浙公網安備 33102402000349號
浙公網安備 33102402000349號